當大腦思緒不受控制時,我們可以怎麼做?關於意識、情緒與身心連結的正念探索

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?當你努力想靜下心來思考一件事,腦袋裡卻像有猴子在到處蹦蹦跳跳,思緒混亂?或是,身體明明有些不舒服,卻總是直到疼痛難耐時才意識到?
在正念的練習中,我們經由一次次反覆的探索,讓「身心腦」三者能夠穩定地連上線。過去,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控制身體、控制思想,甚至是控制情緒。我們以為心智是一個整體,想思考什麼、想控制什麼,都由我們自己能主宰。然而,當我們開始深入呼吸練習時,這個「理所當然」的想法,會被徹底顛覆。
心智的奧秘:意識與思維,為何常常「不聽話」?
邀請正在閱讀的你,試著閉上眼睛,將注意力放在鼻息上,留意氣息從鼻孔的進出。同時,在這個過程,請千萬不要想到粉紅色的大象。
你可能很快就發現,即使你對自己的大腦下達了「專注」的指令,但腦中的思緒卻不受控制地到處亂跑——比如「待會要吃什麼?」、「原訂的工作還沒做完」、「下班要記得去繳費」⋯⋯還有,腦中會浮現粉紅色的大象!
為什麼我們可以輕易地指揮手腳去完成一個特定動作,卻沒辦法下達指令給大腦,要它專注在某件事上,它就乖乖專注呢?這來自某個幕後主角,正是大腦中一個名為「預設模式網絡」(Default Mode Network, DMN)的系統。
我們的大腦有兩種主要的運作模式:
- 專注模式(Task-Positive Network, TPN): 當你聚精會神地埋首工作、分析數據、嘗試陌生的任務,或是指揮手腳去完成一個特定動作時,這個網絡就會被啟動。它負責處理外部任務,讓大腦資源集中在特定工作上。
- 預設模式(Default Mode Network, DMN): 當沒有要執行特定任務,處於耍廢的放空狀態時,這個「自動駕駛」網絡就會自動開啟,思緒會不受控地開始神遊(mind wandering),像個時空旅人一樣穿梭時空,例如:回憶過去、擔憂未來、思考人際關係,或是進行自我反省。
這就是為什麼正念練習時,越想專注卻發現自己越分心:
當我們用意志力(意識)下達「專注呼吸」的指令時,我們是想要啟動「專注模式」,但大腦的「預設模式」卻像常態存在的地心引力一樣,會不斷地把我們的注意力拉走,讓思緒飄向其他地方。
指揮身體動作比較容易,是因為控制肢體動作是一個明確的「外部任務」,可以有效啟動專注模式。但「專注呼吸」雖然也是一個任務,但它是一個非常細微的「內部任務」,一不小心,大腦就會「預設」地溜回它更直覺的自動駕駛狀態,也就是分心走神。
因此,許多學員在呼吸練習中會發現這個「不受控」,這不是個人的專注力不足,從神經科學的發現可以知道,其實這是人類大腦共有的設定。思維(Thought)很大程度上是大腦「預設模式網絡」自動化、不受控的產物,它像是腦袋裡跳來跳去的猴子(心猴 Monkey Mind )。而意識(Consciousness / Awareness)則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覺察能力,像內建了上帝視角一樣,它讓我們能夠「看見」猴子正在腦中喋喋不休,而不是誤以為自己就是隻猴子。
這份體悟,正是正念練習中,往內在平靜靠近最重要的第一步。我們無法讓念頭完全停止,但我們可以選擇,是否要搭上每一班駛過的思緒列車。正念練習能幫助我們重回駕駛座,從大腦的自動駕駛模式中,拿回了選擇權。
正念日常:在「慣性」中看見真實,在「實驗」中滋養身心
將正念帶入日常生活,聽起來簡單,實踐起來卻充滿挑戰。因為這需要我們對抗根深蒂固的「慣性」。
回顧一下,我們每天刷牙、洗澡、走路時,是不是也習慣性地無意識動作?我曾有這樣一個親身經歷。我自認刷牙很認真,但三年多前開始矯正牙齒時,牙醫每次回診都提醒我「牙齒要努力清潔哦」,這讓我很疑惑。
直到有一次,我鼓起勇氣問牙醫:「可以教我刷牙嗎?」我的牙醫告訴我,刷牙時看著鏡子,眼睛跟著牙刷,把牙齒「一顆一顆」刷乾淨。當我開始練習「看著鏡子一顆一顆牙齒刷」,我才發現這真的很不容易,覺察到自己有各種分心、不耐煩、想快點刷完的等「自動導航模式」。這份「覺察」就像一道手電筒的光,隨著細心的探查,照進了我們被慣性蒙蔽的日常角落。
將正念融入日常,有時候比特地空出時間的正式正念練習更困難,但為生活帶來的體驗也更深刻。因為這是將正念從一個專屬的「練習場域」,實際帶入真實生活的每一個片刻。這也很像是生活中有一場持續不斷的尋寶遊戲,在過程中,不斷發現自己從未照見的地方,也隨著一次次新的覺察,我們學會看見自己,滋養身心。
身心合一的語言:情緒在身體上的真實印記
我們都知道生理與心理相互影響,情緒與身體感受之間有著緊密的連結。例如,壓力大時肩膀會緊繃,焦慮時會胃痛,悲傷時會胸悶。這種身心互相影響的連結,在我們感受強烈情緒時更加明顯,卻因為太理所當然了,時常要等到身體傳達出劇烈的感受時,我們才留意到。
我最近的經驗就是最好的證明。我的毛小孩不久前離世,有一天午睡時,我夢到剛離世的毛孩奇奇後,我崩潰大哭。那是一種「撕心裂肺」的痛,胸口緊縮、胸腹腔悶痛,我真切地感受到「心痛是真的」。那份猛烈湧上的孤單感,甚至連結到小時候被獨自留在家中的記憶。這一切都清晰地體現了情緒如何在身體上烙印。
「心痛是真的」:情緒與生理疼痛共享的大腦路徑
過去的研究證實,情緒上的痛苦(如社會排斥、孤立感、哀悼)與生理上的疼痛,在大腦中活化的區域有著驚人的重疊。關鍵腦區如「背側前扣帶皮層 (dACC)」與「前腦島 (anterior insula)」,在我們感受到生理疼痛,或經歷道強烈社交排斥、情緒痛苦時,都會被啟動。
這代表當我們說「心碎」或「心痛」時,並不是單純的文學比喻,大腦在處理這種深層的情緒痛苦時,確實使用了處理生理疼痛的神經迴路。說到這也不禁佩服古人的智慧,有許多描述情緒的成語,比如:怒髮沖冠、如坐針氈、肝腸寸斷、心驚膽戰⋯⋯這些看起來很浮誇的形容,其實都精準地捕捉了情緒與身體感受的緊密連結。人類早就知道,心靈與身體從未分離過,只是現在的科學終於追上了當時的洞察。
哀傷的身體印記:情緒的「軀體化 (Somatization)」
創傷領域的經典著作《心靈的傷,身體會記住》當中,就告訴我們,我們的一切,大腦、心靈與身體,是人類最強大的生存策略,但也正是多數精神問題中崩潰瓦解的部分。在處理創傷時,處理的其實是創傷在身體、大腦留下的印痕,而復原的關鍵,是運用腦部本身的神經可塑性,讓倖存者感受到自己活在當下,並在最終重建對自己的所有權。
延續上段我個人的經歷,人們在經歷失去親人或寵物的巨大哀傷後,情緒常常會透過身體症狀來表達,這在心理學上稱為「軀體化」(Somatization)。情緒來襲時感受到的胸口緊縮、胸腹腔悶痛,都是哀傷常見的身體反應。
強烈的壓力與情緒會觸發身體的「戰逃僵反應」,導致一系列生理變化,常見症狀包含胸悶、心悸、肌肉痠痛與緊繃、消化系統問題、疲勞與免疫力下降。在極端情況下,巨大的情緒壓力甚至可能引發俗稱的「心碎症候群」(壓力性心肌症或章魚壺心肌症),心臟肌肉會因壓力荷爾蒙瞬間飆升而暫時性削弱。這再次證明了,劇烈的情緒確實能對身體產生真實且強烈的物理影響。
「以痛治痛」的本能:與「允許」的練習
人腦有一種本能反應叫「以痛治痛」,透過尋找或製造另一種疼痛來蓋過原有疼痛。這在生理學上稱為「反刺激」 (Counter-irritation),是大腦與神經系統的古老本能,透過分散注意力來減輕原有痛感。
像是許多青少年,在青春期面臨身心巨大的轉變,以及學業、同儕、親子、情感等壓力,感到難以招架時,會採取自傷、自殘的方式來緩解痛苦。他們會說「這感覺很爽」、「這會讓我覺得我存在」,因為心裡的痛苦太強烈了,只好製造身體的其他疼痛來轉移這種內心的痛苦。
這個本能反應,與正念練習中「允許」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,需要我們「刻意練習」。過去的本能是透過「製造新的干擾」來逃避痛苦,正念則提供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:不逃避、不對抗,而是溫柔地轉向痛苦,接納痛苦的存在並與之共處。這正是正念練習能帶來深度療癒的核心之一。
透過正念,我們學會利用身體的訊號來覺察情緒。當身體出現不適或疼痛感時,第一個應對步驟就是「觀察」。不急著避開或改變,而是將注意力轉向這些感受,觀察它們在哪裡、感覺如何,並試著與之共處一會兒。這份溫柔的覺察,正是療癒的開端。
正念革命:面對壓力,不對抗,只存在
2014年,美國《時代雜誌》以「正念革命」為封面專題,深入探討這個源於東方禪修的古老修練,如何在現代社會中蓬勃發展。這個專題反映出正念在全世界都逐漸受到重視,這也代表正念不再只是個人的修練,而是在這個快節奏、高壓力的時代裡,我們的社會需要集體的覺察與療癒,培養隨時回到內心,學習與自己的思緒和情緒共處的智慧。
認知心理學的ABC理論指出:事件(Activating event)發生後,人們很直覺地產生情緒或反應(Consequence),而中間的認知(Belief)因大腦為節省能量而被省略,形成「自動導航模式」。這代表我們常常還沒意識到自己怎麼了,就被情緒反應帶著走。
這也反映出為什麼我們過去處理壓力的方式,會讓人很挫折。因為我們直接對抗情緒 (C),卻忽略了背後的認知 (B)。我們習慣於「消滅」不舒服的感受,而不是去理解它們。
而「正念革命」的意義就在這裡,正念提供我們不同於過去應對問題的「革命性」方法:正念不要求解決、改變、消滅或逃避任何事物,而是以開放、接納、好奇的態度,承認這些事物的存在。
我們透過觀察和覺察來處理不舒服的感受,讓身心處於更和諧的狀態,不在內在打架。這是一種全然的接納,允許情緒流動,也允許自己此刻的感受,更是對身心腦的臣服。
三個步驟:勇敢接住生活中的每一個挑戰
面對生活中的不適或挑戰,正念提供三個步驟,引導我們以更健康的方式應對:
- 覺察: 當身體出現不適或疼痛感時,第一步是「覺察」。不急著避開或改變它,將注意力轉向這些感受,像旁觀者一樣,觀察它們在哪裡、感覺如何。
- 調整: 在覺察之後,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見自己的「慣性模式」。我們可以帶著這份覺察,做出微小的、有意識的調整。
- 不做不必要的改變: 有時候痛苦或不適只是一個過程,正念讓我們在看清狀況前,不做多餘或不必要的抵抗。當我們停止對抗,反而能為身心創造空間,讓轉化自然發生。
這種對待疼痛與不適的方式,不僅適用於身體,也適用於我們的情緒。在面對任何壓力或不舒服的感受時,先停下來,溫柔地與之同在,因為這份接納本身,就是最大的療癒。
在正念的旅程中,我們持續學習如何將「意識」與「思維」區分,辨識大腦的慣性,讓正念融入生活的每個細節,看見身心如何緊密連結,並以革命性的正念態度,不對抗,只同在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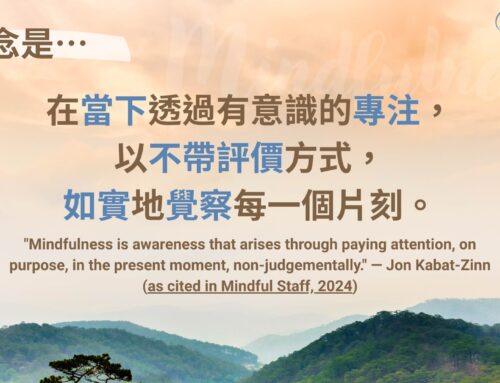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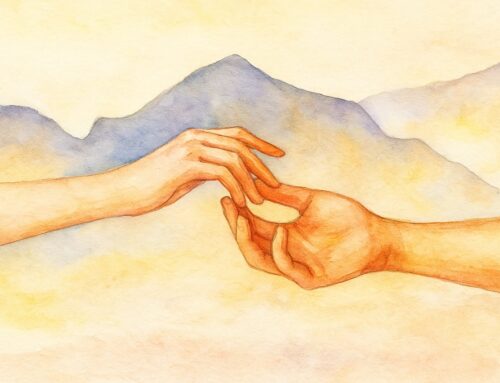
留言